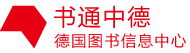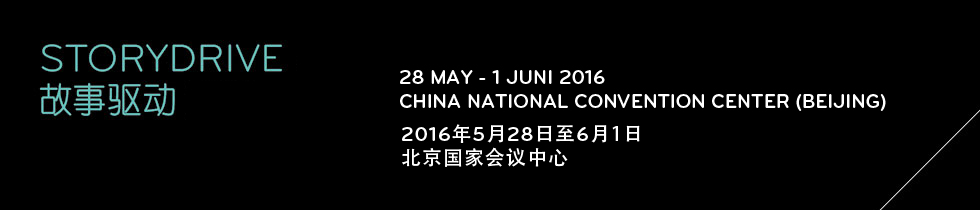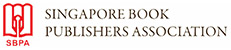媒体中心

8问8答:采访印度尼西亚作家拉什米•帕穆尼亚克(LAKSMI PAMUNTJAK)
原创, 1999年11月30日
故事驱动:帕穆尼亚克女士您好,请问您最近在忙些什么?
帕穆尼亚克: 写和艺术美食相关的文章,这也一直是我谋生的手段。除此之外,目前我还忙于第三部小说的创作。这部小说基本上是我第一部小说《Amba》又名《红色问题》的续集。《红色问题》讲述了两位命运多舛的恋人的故事。1965至1968年间,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反共大屠杀,据估计至少有五百人因被怀疑是共产党人而遭到杀害。 书中两位主人公安姆巴和比诗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失散的。 这部新小说讲述的正是这对恋人的女儿诗莉坎蒂的故事。在书中,诗莉坎蒂是故事的主要叙述者,是一名周游世界的概念艺术家。故事有一部分发生在柏林,也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城市。
故事驱动:在英语版推出之后,您的作品《Amba》最近又被翻译成德语和荷兰语出版,请问市场反应如何?
帕穆尼亚克: 您说的英语版,其实应该指的是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出版的版本。该版本仅在印度尼西亚发行,而且因为是限量版的缘故,现已不再发行。然而,《Amba》也就是《红色问题》的美文版将于今年七月在美国出版。 德国和荷兰市场反馈是非常积极的,这令人感到意外。这部小说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,特别是在德国,销售数字之高出人意料,头三个月就卖出了超过一万本。不仅如此,评论界对这本书的反响也非常好。这部作品不仅进入了《法兰克福汇报》评选的法兰克福书展最佳小说排行榜,而且还出现在奥地利国家广播公司和德国《图片报》评出的10部最佳小说名单上。作为由德国以外作家创作并翻译成德语的作品,它还在《世界最受欢迎图书》榜单最佳虚构类作品分类中名列第一。这个榜单是由德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确定的,因此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。
不过最棒的还是我去年九月、十月在德国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的巡回推广活动。这期间,我不仅到访了德国许多城市,而且再一次意识到德国社会的富有教养与丰富多彩。可以说,德国社会是一个读书人的社会。
事实上,无论走到德国的哪个地方,无论是柏林、汉堡、杜塞尔多夫、哥廷根、比勒费尔德、波恩、埃尔福特、海德堡、法兰克福或是巴德贝尔莱堡,我遇到的德国人都对印尼人的遭遇都富有同情心。印尼人一边努力接受我们暴力的过去,一边也努力给很多不为人知的受害者还以有形的公正。这就好像两个缺少共同历史的国家,仅仅通过民族创伤的经历,就能在情感上和精神上获得共鸣。
故事驱动:一本书如何才能走出国门?您在写作的时候,会考虑到国际市场吗?
帕穆尼亚克: 这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。当然,在没有合适译本,特别是英文译本的情况下,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。事实上,翻译的质量至关重要,它可以成就一本书,也能毁掉一本书。
我也认为一定的易读性,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,一定的“普遍性”是很重要的。同时,作品也应充分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。但是如果缺乏引人入胜或打动人心的情节,外国读者是不会买账的。也就是说“新鲜感”也同样重要,特别是如今国际市场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、可以让人“普遍接受”的故事。你的作品必须在某些地方显得与众不同,你的声音必须得是独一无二的。不过,对于独特内容的多少,你还需要有分寸感,以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。比如说,不要给外国读者太多的历史负担,或给他们过多叙述文化的特殊性。 虽然这样说,我却相信好的故事可以而且应该跨越国界。当然这需要技巧,特别是讲故事的高超技巧。我必须承认,在创作《Amba》的时候,我遇到的困难不仅局限于为小说找到恢宏的主题,克服写作初期那种创作没有经历过的故事所感到的胆怯,还有第一次创作小说,极其缺乏经验这个直白的事实。怪不得我一直还在纠结用哪种语言进行写作! 一开始,我用英语写作这部小说。我都不记得这部小说一共有多少个版本。设计了无数的开头和结局,各种版本的人物重点描绘及走向。一段时间之后,这部小说才有了我认为必要的结构。
接下来还要面对语言问题:对于背景如此丰富的历史,在用另外一种语言撰写或改写它的过程中,信息总会有所遗失。许多当地笑话,各种对话、交谈、历史细节以及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其实没办法翻译,因为它们太“特别”。那些可能只在印尼读者,或者至少熟悉印尼历史的读者中间获得共鸣的地方特色和风格,确实难以翻译。将一个故事翻译为不同语言、不同场景和不同历史的时候,仿佛总有着难以避免的残缺。 我认为在这一过程当中,我掌握两种语言这一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对英语的热爱常常令我感到与自己的印尼语境疏远了。我的读者既有说英语的,也有说印尼语的,这让我无所适从。因为当我在用一种语言写作的时候,我却在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思考。在创作《Amba》的时候,这种情况尤其令人不安。
正是在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下,我想,哦,也许我需要用印尼语创作小说。这样我才可以更好地适应这些特殊性,并与印尼读者进行分享。
故事驱动:您似乎是典型的中国人所说的万事通:您既是一位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,又是美食作家,还曾是古典钢琴演奏家——这里我可能还遗漏了其它一些职业。这些职业当中,您最喜欢的是哪个?为什么?
帕穆尼亚克: 我觉得我对任何一个行业或领域的喜爱都不会超过其他行业。换句话说,我没有最喜欢的行业或领域,它们之间是相得益彰的。
作为一个曾经沉浸在西方古典音乐传统中的钢琴演奏家,音乐的语言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词汇,并以更为直觉的方式给予我声音、节奏和乐感的体系。而这是我在写作时一直孜孜以求的,尤其是当我创作诗歌的时候。
关于美食的文学创作也得益于我对绘画和视觉艺术的热爱,以及我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和熟知。反过来,作为一名专业美食鉴赏家,鉴赏美食时的味觉体验也极大地提升了我的诗歌表达。
但是,如果说有一种事物能将所有这些职业联系在一起,那就是语言,是我对写作和阅读的热爱——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无论最初是什么激励我去创作,没有什么能比流畅的语言能带来更大的喜悦。
故事驱动:无论在哪里,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都在快速发展,这改变了您讲故事的方式吗?您认为故事讲述的未来在哪里?
帕穆尼亚克: 我当然更喜欢风格简洁、节奏恰当的讲述方式。讲故事时,应该尽快说到点子上,在不影响艺术性的前提下实现“加速思考”。事实上,真正的艺术在于精准。现在大家都缺时间,没人有时间看拖沓的作品。虽然如此,我依然欣赏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,那些大部头的鸿篇巨作,它们的广度和深度正是其非凡之处。那些伟大而永恒的作品,你甚至无法改变其中的一个句子。
故事驱动: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艺术家或作家?
帕穆尼亚克:我很喜欢沈伟的舞蹈编排。对于视觉艺术,在老一辈艺术家里,我喜欢常玉、吴冠中和赵无极的作品。年轻艺术家里我喜欢严培明等人的作品。
故事驱动:您最喜欢的中国菜是什么?您对印度尼西亚的中国餐馆有什么建议吗?
帕穆尼亚克: 我没法选择!如果必须选择的话,有两道菜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有很多个版本,而且我也多次品尝过,那就是炒河粉(这道菜非常流行,甚至有人认为它属于马来半岛,因为这道菜已经根据东南亚人的口味进行了充分的改造)和海南鸡饭。
而且我也离不开广式茶点,每个月都要品尝一次,在雅加达有很多十分不错的茶餐厅。 但人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,印尼风格的中国菜绝对是世界上最棒、最美味的佳肴。请到印尼棉兰、坤甸、泗水甚至雅加达的任何一家有人气的海鲜餐厅品尝一下,您一定会知道我在说什么!
故事驱动: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吗?您对本次故事驱动大会和中国之旅有什么期待?
帕穆尼亚克: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。我第一次去北京是在1994年,当时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,大概有三周吧。但是那次很不幸,我来北京是为了陪伴我已故的姑妈,她当时正在接受癌症治疗。不过很幸运,我当时还是去爬了长城,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。后来,2002年我又一次来到北京和上海,那一次行程就比较开心。
我迫不及待想再一次访问中国,这离我上一次到访已经相隔十四年的时间。这段时间里,我听说了太多关于中国的报道:中国的改变之多、变化之广、变革之深、发展之快,以及它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影响之深远,甚至通过新闻报道都无法彻底了解。虽然三天的访问时间太短了,但是我仍然非常期待这次与北京的重逢!
拉什米•帕穆尼亚克 (LAKSMI PAMUNTJAK) 将作为演讲嘉宾参加5月29-30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故事驱动大会。
翻译:汤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