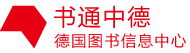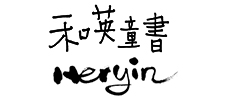采访报道

六问六答:采访周逸芬
1. 周女士,您最近在忙什么?
最近在进行十二集儿童电视节目的结案。
2. 您是哪一年开始做图画书的?当时是如何开始的?这些年中图画书领域最大的变化有哪些?
我是公元1998年开始做图画书,由于学生时期编过校刊、系刊,编辑的过程蛮自得其乐,再加上小时候家里很多优秀画作,潜移默化之下,很早我就把图书编辑,当成自己的志向。但是从美国回台湾后,我先生在(高科技城市&文化沙漠)新竹科学园区工作,而台湾的出版社都在台北,所以我只好在新竹给自己创造工作机会,成立了和英出版社。
在我做图画书的二十年中,前十年(1998-2007)图画书属于开拓期,最近这十年(2008-2018)图画书逐渐步上坦途,尤其原创图画书在质量、数量、读者接受度,都有长足进展。比如2002年和英出版第一本原创图画书时,做了许多配套的赔本措施来护航。但随着原创渐入佳境,2005年起逐步减少赔本措施。
在销售模式上,台湾图画书约2000年起逐渐从(直销)套书模式,走向在书店(包括网络书店)单册销售模式。这意味着每一本书的质量要禁得起读者一本一本仔细检视。
3. 如何理解图画书的跨界?和英在儿童音乐和动画方面有哪些尝试和成绩?
每个人在不同阶段,会有不同的使命。
和英最初十年,就是单纯出版好书。
但最近这十年,是以图画书为圆心,借由跨界把半径拉远、想画出更大的圆、做一些别人(因为没利润)不愿意做,或没有余力做的事。
跨界的过程很缓慢,比如历时十年完成的《永远的儿歌:米米听民乐》获金曲奖最佳儿童音乐专辑奖、《永远的杨唤》获金曲奖四项入围(最佳作曲、最佳演唱、最佳演奏、最佳专辑)、历时十年刚完成的米米精致动画,获欧洲国际集团青睐,将有深度合作。
4. 为诗歌配上插画是和英的独创吗?《一枚铜币》在2017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获得全球插画奖后,相关图画书的销售是否提高了?
为诗歌配插画,在欧美已有许多佳作,比如《雪晚林边歇马》(佛洛斯特名诗、余光中老师翻译)。在华文世界,不清楚是否和英独创,但坊间的确更多是“一首诗配一幅图”,这样好像较难引起感动并发挥绘本特质里“如跳水的剎那美感”。
乌猫老师画的《一枚铜币》获奖后,《余光中诗画集》无论在销售或人气上都大幅提高,我们也乘胜追击,在FB脸书上做了大幅推广与宣传。很庆幸余老师亲眼看到他的诗的插画获奖。
5. 对于2010后的一代或者更远的未来,传统图画书还会保持今天的市场地位吗?
回答这个问题,得回溯二十年前做儿童图画书的初衷。我是学幼儿发展心理学,我在乎孩子的需求。一直认为儿童图画书只是一个媒介,醉翁(幼儿)之意不在酒(书),孩子真正需要、真正想要的,是父母揽着他共读的温暖与爱。
幼儿的这个需求即使在更远的未来,也不会改变。因此传统图画书还会有今天的市场地位,但亲子共读的图画书形式,会更多元。
6. 绘本可以被数字化吗?
在特定条件下,绘本可以被数字化。绘本数字化的前提是,它不是幼儿的主食,是零食(也就是辅助品)。幼儿每天需拥有充分感官经验与活动,比如玩泥巴、堆积木、荡秋千、滑滑梯。主食吃饱了,才吃适量的零食。
和英跨界创作了许多儿童音乐和动画,这些都是国际化的“基本配备”,也是做儿童音乐剧的“素材”。比如父母带孩子一起欣赏儿童音乐剧,图画书中的角色由大型人偶(或手偶)扮演,舞台背景是多媒体动画,主角们演着图画书故事,唱着好听儿歌。这样的亲子同乐,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宝贵经验。
还记得十五年前,我曾问一个畅销图画书画家,我是否可以印五千册他创作(和英出版)的图画书,捐给偏乡弱势孩子,他拒绝了我。于是我开始策划一系列自有版权的书,并尝试自己写作。后来我准备了一百多万台币,去印制捐赠的图画书,只印了一种书就把预算用完了。当时我就想,如果是捐一片光盘(里面放五十本书),是不是会有千倍的偏乡弱势孩子可以享受图画书的美好?
周逸芬将作为演讲嘉宾参加2018年5月28日-6月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故事驱动大会。